
风流一代剧情介绍
风流一代评论
 甜心♀莼莼
甜心♀莼莼真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问贾樟柯是不是以前有个暗恋的同桌名字叫巧巧,然后被一个喜欢看录像混迪厅打台球听叶倩文粤语歌的名字叫斌斌的学霸撬走坐绿皮火车去了三峡,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请贾科长正面回答这个困扰我很多年的疑问,不然我会继续问下去,直到贾科长回答我为止。贾科长,我知道你看得到,站出来
 星辰璀璨
星辰璀璨##LFF 整体呈现出的感觉非常好,实在是太爱这个结尾了,影片以跨越20年的素材制作,像是一部风情画,女主的行走有蔡明亮行走系列的质感,当然科长之前也有部《海上传奇》也是这种行走的作品。
由于时间跨度很大,感觉也是作品比较有力量的地方,因为流动的时间没有饶了任何人,一切都像他在QA时所说的趋近于真实。赵涛对于角色的呈现非常好,尤其是结尾的情绪表达。
视觉上,很多种不同的介质带来了不同的画幅比例,最古早的是4:3呈现,两边儿带黑边,后续同样的2001年的则切换到了宽幅两边的黑边消失(当时申奥成功了),再之后则是同画幅下的清晰度明显高了不少,这是更加接近现在的时段了,最后则是疫情和最后上下都有黑边的宽画幅,这一切像是观众一下扎进了导演的硬盘中保留的记忆里,镜头是比较常规,运动镜头很流畅,跟机器人的对望科长在QA做了解释,很多素材也使用过在他之前的作品中。不咋喜欢的是监控器投下的那种僵硬的环绕镜头,可以理解是科技的体现,但是感觉更像是批判。
听觉上,配乐的选择是非常符合城市变化和剧情发展的。比较震惊的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本身是下岗潮和国企改革后的生活表达,仁科和阿茂那段儿则是追忆爱情的呈现。由于是风情画,所以配乐还是蛮重要的,感觉这部作品呈现的很好。最精髓的是女主一直沉默到最后的那一声喊,喊出了压抑了大半部电影的情绪。
Tony Ryans字幕做的真不错,他给很多侯孝贤的电影做过字幕,而且他本人也到了现场,然后也发现Chris Berry也在现场,蛮有意思。
QA,20年间的素材是在疫情期间数字化并回顾的,介质有很多,DV,35mm,16mm也有照相机拍的,之后才从头看,给导演的感觉是熟悉又陌生,因为很多经历的20年后回顾那些场景都已经忘记了,他说看素材的时候像是坐上时光机,但也只是过去的灰烬。
剪辑时是一屋子的硬盘,组织的过程是十分困难的,疫情期间他还做了一档网络的节目,让他觉得导演本人跟人工智能很相似,以他拍过的电影可以构成一个影响世界,就让导演感觉非常自由,他可以把素材赋予新的意义。
观众提问,还是很有表达欲…本来能精简一下,非要提自己的经历…就好好问问题得不到同样的答案么?
科长也说因为是拍摄方法的问题,自己更加容易沉浸在空间中,如果文字到影像要强调叙事性,但当去除了叙事性后,注意力会更加有存在性。
PS:现场的翻译超级强!
 清风拂面梦中行
清风拂面梦中行时隔6年后贾樟柯导演携《风流一代》重回戛纳,第六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是本届主竞赛唯一入围的华语电影。贾樟柯利用2001-2022年自己拍过的影像素材,横跨22年之久,回溯重构了从《任逍遥》起始的创作脉络。
正如克劳考尔曾言:“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原”这一基本命题出发,阐明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和提示我们周围的世界。”贾樟柯透过《风流一代》沉默得再现了纪录了历史洪流中他所感知到的某种真实。
同样是聚焦于“时间”“变迁”,正因为影片的拍摄形式,制作概念的全新角度,让观众对于贾樟柯电影有了全新的感受。不同于密集台词营造的冲突感,电影通过超长时间跨度的新旧影像,持续记录时代的变化,并巧妙融合承载时代记忆的、风格化的音乐,将摇滚精神贯穿影片创作。
《风流一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观众“讲故事”,而是让观众“戴上VR眼镜”,通过贾樟柯的“眼睛”沉浸式的旁观这对普通人的半生,以及中国飞速更迭的20年。
戛纳电影节期间,抛开书本有幸采访了贾樟柯导演,从简短的访谈,以及媒体发布会上的发言里,我们将一起感受贾樟柯的新电影宇宙。
采访:忠泽、陈磕碜
整理/编辑:许珂
视频剪辑:嘻璇
音频剪辑:猴听听
排版:妖妖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抛开书本X
贾樟柯
《风流一代》戛纳采访
Q:抛开书本:
贾导好,想问一个关于您和赵涛老师合作方式的问题。之前在《江湖儿女》的洛杉矶映后,您讲到,您是拿着本子去请示赵涛老师说,这是一个有些犯罪元素的角色,看她有没有兴趣演,她后来跟您说,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可以演。她也承担了很多关于这个角色塑造的具体内容,比如横跨二十年的皮肤材质、妆发。
所以想问一下,在这次《风流一代》,您和赵涛老师是怎么达成合作的?是拿着本子,还是说先有了之前拍摄的一些素材?
A :贾樟柯:
这一次是拿着粗剪加本子。因为我们前面没有本子,前面完全是在素材里形成叙事的。
珠海之前的部分,真的就是剪好之后,我们拿着这个粗剪,再拿着22年当代部分的剧本给她看。当然她也无法推脱,因为前面2/3都是她演的,后面不可能换人了(笑),那也没什么可商量的,最后就完成这个电影
Q:抛开书本:
刚刚看这部影片的首映,可能没法理解这个影片中,女性角色刚开始放弃自己的生活去追寻男人,类似于工具化的角色,就像您前面所说的,是在浪潮中被困住的人。
那您觉得,这还是中国大多数女性的困境吗?她最后又是怎样的内心转变?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角色设定的?
A:贾樟柯:
波伏娃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她说,没有天生的女性,女性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认定。就这个电影而言,它是一个有二十年跨度的电影,其中的女性也不是天生有女性意识,她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获得了女性意识。
所以我觉得她的变化,从一个依赖感情的人,然后被伤害,到寻找感情,到断然分开,再到我们可以想象,她人到中年以后,或许就变成一个人生活,她可能都不需要男女关系了,甚至我觉得她会花心等等,都有可能。
当然这不是电影交代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说,呈现女性成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让我特别着迷的事情。
反过来说,我们拍得杂七杂八的方向可以剪成很多不同的电影,在这么多的素材里,为什么就觉得赵涛饰演的巧巧,那么吸引我们剪下去?从她的外表、从我们拍摄的不同阶段的情景和剧情里,能看到她变得越来越强悍,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本人慢慢理解女性的一个过程。在这样大的一个时间跨度下,巧巧便有这样的一个成长与转变的过程。
《风流一代》
戛纳发布会
追溯《风流一代》的缘起,贾樟柯说道:“最早是2001年就在制作一部影片,叫《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因为那时数码摄影机刚刚出现。我们想带着这台摄影机,去到中国我喜欢的城市进行拍摄。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漫无目的的拍摄,延续了很多年,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这个过程中,除了记录的段落,也会带着演员们拍一些情节性、故事性的部分,但它非常散乱,因为它就是一种即兴的、随意的拍摄。
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到疫情期间,突然想观看这些素材、剪辑一部电影,慢慢在剪辑的过程中,形成了现在这个电影,叫《风流一代》。
赵涛在《风流一代》中饰演巧巧。当被问及巧巧的角色塑造时,赵涛说,在刚开始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并不太清楚她要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看到剧本、跟导演交流之后,她了解到,她在《风流一代》里面饰演的巧巧,是被设置为一个超市里面给水果称重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特别想拍出人物的一种生命的落差感。”赵涛说道。所以当她了解了导演的一些想法,在超市体验了生活后,就能特别感受到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
赵涛认为,正如此部影片的英文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一样,为潮水所困,《风流一代》里面的巧巧,就是一个被困住的人,第一是她为丰富的物资所围困,第二就是她被不同的人、顾客一直包围着。巧巧的生活比较艰辛,但是因为疫情,对于工作还是非常珍惜的,所以这一次她饰演的巧巧,总体来说是一个被困住的人物。
今年,贾樟柯第六次以导演身份入围戛纳电影的主竞赛单元,同时以演员身份,在管虎导演的《狗阵》中饰演角色,这部影片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
当被问及对自身双重身份的体验,贾樟柯导演说道:
“我很荣幸参与了管虎导演的《狗阵》的拍摄工作。我不是一个专业演员,虽然我是一个导演,但表演确实不在行,但是最近几年,很多导演朋友有一些不重要的角色会邀请我去演,我也很乐意,因为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电影这个工作,从演员的角度去感受制作过程的快乐。
我也参与了管虎导演在影片之前的一些行程跟仪式,以演员的身份也有机会观察,一个导演带着作品来到电影节,要跟第一批观众见面的那样一种兴奋和忐忑。反过来,我(作为导演)也要接受第一批观众的检验,这种感受混合在一起,让我觉得非常有仪式感。
特别是这两部影片,都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我们的整个制作都耗时很长,因为拍摄、制作都不是那么方便,经过好几年,疫情也过去了,我们也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带着影片回到国际视野,还是觉得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还是需要通过电影分享给更多人。”
《风流一代》的素材,具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贾樟柯表示,这些影片最早的素材,都是记录在磁带(tape)上。那时候虽然是数码,但是它还是储存在磁带上,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从处理早期影像开始的,他们把这些影像从磁带转到硬盘,这一过程中,制片部门克服了很多技术性的难题。因为这些素材积累了很多年,所以到观看的时候,更是一段段尘封的记忆。
贾樟柯讲述了他的几个具体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恍如隔世。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二十年,但是很多已经遗忘了,再看的时候,它激活了你对那个时候的记忆,恍如隔世,物是人非。第二个印象,我觉得人的形象变化很大。
2000 年初,其实数码摄影也不成熟,我们拍摄的也是一个即将变革的生活,是在一个变动的开始,也没有成型,媒介与当时人的状态,完美地融合到一起,我自己就会觉得,2000 年之初的中国,特别适合数码去表现,它充满了能量和一种莫名的激情,大家都懵懂地憧憬着,向往未来。这样一种社会情绪,与数码这个影像本身就契合了。
至于剪辑,它就像盖房子一样。怎么去选择(素材)呢?在盖的过程中,你觉得这儿需要这块砖,那儿需要那片瓦,就在我们海量的素材里找来找去,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感性的工作,因为除了要考虑叙事之外,还要考虑视觉的元素、声音的元素,很多都是同时的判断,而这个判断,主要是感性的判断。确实是一砖一瓦,拎来拎去,剪了三年,把它完成了。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影评说,这有点像织毛衣,我觉得说得很对,确实有点像织毛衣,是手工做出来的。”
贾樟柯的作品中,《江湖儿女》和新作《风流一代》的结尾呈现相似的情节,但巧巧的情感态度与情感张力并不同。在媒体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问,赵涛表示,贾导很喜欢让他电影当中的人物都叫作巧巧,她也很习惯,但从创作层面来说,每一个“巧巧”都是不同的。
赵涛说道:“《江湖儿女》里面的巧巧,她的人物设定非常明确,她是一个所谓的黑帮老大的女人,所以她是非常有活力、有冲劲、有爱、有恨、有仗义的女性。而到了《风流一代》里面的巧巧,特别是结尾的时候,我觉得结尾的那一声呐喊,实际上是把《风流一代》里面巧巧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情感释放出来了。
这个人物在电影当中,一直没有说话,但不代表她没有话讲,而是她不愿意去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我理解这个人物的时候,最后那一声呐喊,不光是对于巧巧,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想释放的一个声音。”
作为团队中很年轻的工作人员,万佳欢表示,对她来说,这一次的剧本工作特别特殊,整个项目是从影像开始的,所以剧本工作其实也是从影像开始的。“我们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我们跟贾导一起,看了差不多 1000 小时的素材,这并不是很标准的剧本创作流程。我们的素材本身非常丰富,非常庞杂,我们要从里面找出这个叙事的线索。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贾导想要完成一个怎么样的影片,然后我就问了他,你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呢?
他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他说他想做一个故事片,并且想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片,人物的生命线索可能会让你觉得似曾相识。但是呈现的方法,包括最重要的视听语言、结构,都需要是崭新的。那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可能要用反类型化叙事的方式,来做一个新的叙事创作。”
在第一个阶段的工作里,万佳欢与团队成员梳理出来人物的命运线索,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确定了线性的叙事结构。这个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方法,但在一开始,他们就特别坚定这个结构。
万佳欢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看素材的整个过程,就是时间线性的。这让我们非常感慨,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会变化成这样,一个社会会变化成这样。第二个原因,我们当然可以尝试采用一种闪回的、回忆式的、美国往事式的结构,如果说采用那种结构,可能会增加怀旧感。但是我们会觉得,它削弱了这个剧本、这个电影本身的纪实的力量感。
前 2/3 的影片,其实是在剪辑台上完成的,后来的剧本创作,就是在反复地观看前剪辑段落的基础上,带有一点忐忑地写 2022 年的两位中心人物的命运。但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前提,要保证影片叙事的整体性,我们觉得最后做得还不错。这就是整个剧本的创作过程。”
发布会最后,贾樟柯表示,寻找新的电影方法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个简单创新的问题,是一个表达准确性的问题,因为社会新的变化、人类新的情况,它必然要求我们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去表现它,最新的人类状况,用老的电影语言可能往往是表达不准确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新的感受一定会带来我们对于新的形式的需要,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才去找新的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驱力之下,我们会不断地打破成规,即使制作的是观众不太习惯的电影,但是你触及到了一种新的方法之后,很快观众就会习惯。
所以这样的电影,它需要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语言。"
 樱花の泪ヾ
樱花の泪ヾ贾樟柯将万青和五条人融进乡民图景、启用年轻剪辑师、将自己的人文关怀藏在人机对话,都是他的自我更迭和改造的体现。 他将女性作为一个政治、历史、文化的汇合点,一个“脆弱”又“坚强”的载体,在抽离她的声音之后,贾樟柯也失去了回声,女性和所谓的时代话语碰撞的时候,赵涛的反应就是“木”,以及雨中某个意味并不深长且诡异的笑,以至于到最后口罩覆盖住表情,机器人都只能将赵涛解读为:“对不起,我看不清你的表情”。多个似曾相识的情绪高峰的场面被镜头截断,避免了直接的情感冲突,但是贾樟柯又无数次暗示了情感的存在,so close yet so far,情感顺着某种流逝的河水、某班列车和记忆叠化在一起,看得出来时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痕迹在贾樟柯身上显形。不过,最后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情绪语法的人可能早已死去,剩下来的仿作就只能无数次挪用修正记忆,改造文明话语,试图填补英雄时代逝去后的空白。
 笑着说滚吧
笑着说滚吧 少年呆萌可爱
少年呆萌可爱 琴瑟和鸣醉华年
琴瑟和鸣醉华年 浮华的背后
浮华的背后 暗夜星辰
暗夜星辰 森林的秘密
森林的秘密 沉默的画笔
沉默的画笔 雨打芭蕉声声碎
雨打芭蕉声声碎 灵魂的音符
灵魂的音符 宠爱↘白痴
宠爱↘白痴
 正片
正片 正片
正片 正片
正片 HD中字
HD中字 正片
正片 正片
正片 正片
正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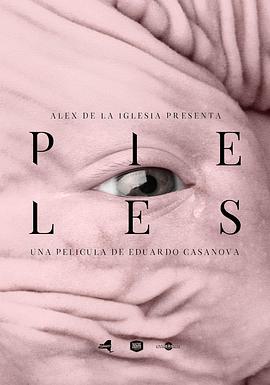 正片
正片 更新HD
更新HD 正片
正片 更新中字
更新中字